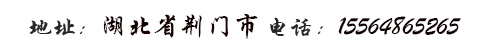治疗的最高境界从瓦解邪恶同盟始Bette
|
白癜风涂抹药物 http://pf.39.net/bdfyy/tslf/171203/5897881.html 文|王烁 一 每个家庭都经历过我的这次就医。 二宝蔫了。 摸额头,烫手。测体温,39度多。医院赶。 其实,二宝医院。咳嗽已经三个月,医院先看的是位外籍女医生,听诊器胸前背后听了很久,说是有些支气管肿胀,其余无大碍。为了确保我们理解,还手绘了上呼吸道和肺部的草图。开了点药给二宝做雾化,好让呼吸顺畅点。 现在二宝高烧了。为什么? 急诊室里,大夫做了血常规检查,又给了点退烧药,服下后要观察半小时。等待结果时,这位中年男大夫跟我说,二宝多半是上呼吸道感染,喉咙里呼噜声是有痰。血检是为了判断是不是细菌感染,如果是细菌感染,才会考虑用抗生素;如果是病毒感染,那就没有特效药,只能对症治疗。 什么是对症治疗? 医生说,与对因治疗相对,对症治疗只能缓解症状,对二宝这次来说,就是降温、怯痰、舒张支气管之类。至于对付病因,就要靠自己的免疫力了。 我恨不得把二宝托付给医生你,而你说二宝还得靠自己? 医生看我表情迷茫,说,其实治疗小朋友是其次,主要是治疗小朋友的父母。 这是真的。 大夫接着说,我也有孩子。如果我是你,如果小朋友体温降下来了,建议回家观察。回家后体温在38度以内,擦身,多喝水,物理降温;38度5以上,吃退烧药;只要孩子精神好,就不会有事,如果精神忽然不好了,医院。他把电话留给我,有任何事随时打电话。 “如果我是你……”,这句话是医生能给病人最诚恳的建议了。 半小时后,体温降了,我抱着二宝回家。第二天一早,医院,见到第三位医生,一位老大夫。听诊,血检,全套又来了一次,对此二宝已经很熟悉,看见护士过来,先发制人地哭了。护士趁机取了点二宝的鼻涕,多做了一项合胞病毒检查。 结果是阳性。 医生和我都长出了一口气,确诊为病毒引发的肺炎。医生最担心的是不确定,我最受不了的也是提心吊胆。 二宝几个月来一直有这些症状,医院,做遍了过敏测试、细菌感染测试、病毒感染测试,从来没有得到过确切结果。医生们含混地说:可能是细菌感染,可能是病毒感染,可能两者都有,可能,可能,可能,但从来没有检查结果的确切支持。 这次好歹确诊。 对付病毒感染,回到”对症治疗“。医生开药与此前其他医生开的并无多大区别:一味烧药降温,一味雾化扩张支气管,一味止咳怯痰。我给二宝用类似的药前后好几个月了,凭什么这次会有效? 我没有追问,知道答案是什么:第一,一岁多的小朋友本来就没有多少药可以选择。第二,那句老话:对症(状)治疗,解决症因靠自己。 三天后,缠绵二宝近三个月的症状,那些咳嗽、呼噜呼噜的呼吸声、流不完的鼻涕,消失了。 我想知道它们为什么消失,只要消失。 又一次坐在年长医生前,为二宝复查,医生听完叙述,在电脑上敲了一会儿,说,我还是把诊断改为支气管炎吧。 原来医生也不知道。 二 我看到了这些: 第一,医生是非常专业的共同体,接受同样的训练,分享同一套知识体系,按同一套规程操作。二宝几个月来见过七位大夫,诊断和治疗遵循同一套流程,同一根决策树:发烧?血检结果?病毒检测?根据检查结果决定走决策树接下来的哪一个分叉。另外,他们都尽量避免给小朋友使用抗生素,尽量不拍X光。 第二,哪怕是如此常见病,大夫们判断也并不相同。有的认为是支气管炎,有的认为是肺炎,有的认为两者都有。而病因,有的认为是病毒感染,有的认为病毒和细菌感染都有。显然,医学不是一门精确科学,而治疗是摸着石头过河。 第三,治疗这件事,结果当然最重要,但如果治疗不是一个药到病除的事情,而是在隧道中前行的旅程,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、难决的取舍,最终仍是在许多不好的结果中找到一个不是那么不好的结果,那么,医生与患者如何一起走过这个旅程,也至关重要,有时简直同样重要。 每一次治疗都有三层:治病本身;治疗的决策过程;患者的情绪管理,而贯穿始终的,必须有信任。 三 病人检查出癌症,恶化速度很快,必须要马上做决定。坐在候诊室里,满怀恐惧,周围都是癌症患者,一个比一个病重,病人仿佛看到了下场。轮到他了,医生叫进去,又做了点检查,然后谈话,满脸疲态。 医生说,你这情况很常见。 死亡,对病人比天还大,对医生只是个数字变动。这不是谁的错,所处位置不同,看问题角度有差。 可命是你的,怎么办呢? 治疗决策,人生最想回避、准备最不足但又最重要的决定,太沉重。 四 如果疾病带来的苦痛有十分,那么直接间接地,至少有五分要归于信息鸿沟。 在魏则西悲剧中,百度-莆田系-医院组成的利益链条,无一不是利用信息操纵牟利。百度假装提供中立的搜索信息,其实是放任、默许、纵容骗子,收其买路钱,向其导流;骗子假装提供先进医疗服务;医院则是外包科室,向骗子出售声誉。最后,患者入毂,被榨取最后一点价值。 这条由信息操纵钩连起来的邪恶同盟存在了很久。对中国医疗体系做任何手术,都必须将其瓦解,但这仍只是病人良性医疗决策的起点,远非终点。 健康扫盲(Healthliteracy),病人作循证决策,而不是靠道听途说的故事。它至少包含三部分,第一,了解治疗数据的含义,得有一点统计学常识;第二,了解数据的呈现方式,导向对患者决策影响很大;第三,了解治疗方案的风险。 充分告知患者病情及各种治疗方案利弊,然后了解患者的需求,再制定治疗方案,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部称之为知情患者偏好,高质量治疗的标准。即便如此,也只是走到了中途,困难贯穿始终: ——面对急症重症,患者必须做重大决策,而这常常是一次性的、不可逆的;比如,手术成功能治愈,但手术本身有20%的死亡风险;不动手术则有80%的风险活不过5年。没有谁擅长在这般两难前作选择。 ——更何况,治疗方案的风险收益时常无法量化; ——哪怕医生医德高尚,医生与病人的目标天然不尽重合。 JeromeGroopman专注研究医生与患者的医疗决策,曾写过HowDoctorsThink,讲医生思维,YourMedicalMind:HowtoDecideWhatisRightforYou则从患者角度着手,运用认知科学方法,分析几十位病人作出医疗决定的过程。 书中有一位患者,本人是企业战略顾问,决心把商业决策逻辑与流程用于自己的医疗决策,结果放弃:医疗决策跟商业决定完全不同,无法做到像后者一般理性。 第一,疾病的所有方面都了解清楚了吗?第二,了解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吗?第三,医生和病人共有清晰的目标吗?第四,各种治疗方案分别有何后果都了解吗?第五,对结果有没有客观的评估标准? 答案都是否定的。 这是患者的天问,也是医生心中最大的无底。医生不担心死亡,它每天都在眼前发生。如果风险确定,不论多高,医生并不担心冒险,如果舍开刀无他途,那开刀就是。可治病几乎没有这么简单的时候,它是一连串的权衡取舍,而在这条路上,医生和患者共同最担心最害怕的,就是不确定性:在无法量化的诸风险中,作出不可能完美几乎总会后悔的选择。 五 医疗决策如此之难,信息不对称如此之高,深刻地刻画了病人与医生的关系。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,以中国当下为最,但它在哪里都不陌生。病人热望找到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,把自己彻底交给他。一开始神化医生,治疗无效又妖魔化医生,根源在此。 医生既非天使,亦非魔鬼,跟患者一样,是凡人。 人各有天命,治疗只能首先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hiqiguankz.com/zqgkzkx/1922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PPT一例重症支气管炎合并低氧血症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